《紅樓夢》已無家可歸?
稱贊者認為把寶玉出家放在開頭、將寶黛初見留待片尾是巧妙的設置,并用年輕人喜歡的愛情敘事來詮釋悲劇。吐槽者則認為這是在復制87版(指1987年電視劇版《紅樓夢》)的經典場面,以短視頻的方式完成剪輯,而故事主線卻又是“陰謀”與“愛情”的混雜,演員表演、人物妝容和布景都給人“怪異”的觀感。截至8月25日晚10點,一萬三千余人在豆瓣參與評論,目前評分4.0。評分低于2010年李少紅導演2010版(5.8分)。

《紅樓夢之金玉良緣》(2024)劇照。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在過去兩百多年間,無數人成為曹雪芹的忠實讀者、癡心“紅迷”。《紅樓夢》的文本也經歷了多番改寫,最著名者為程偉元和高鶚所整理版本。早期戲曲的改寫則讓《紅樓夢》有了可視的版本。隨后電影、電視劇全面生產了“可視的《紅樓夢》”。
或許很多書友都曾記得當年2010新版電視劇《紅樓夢》開播之時,觀眾評論該劇畫風“詭異”,并質疑演員的妝容和表演。如今電影改編版《紅樓夢之金玉良緣》所受的否定似乎比14年前的新版電視劇還要多。

《紅樓夢》(1987)劇照。
是否因為87版開播在先,已經塑造了人物形象,此后的改編再也無法獲得人們的認同?這種簡單的歸因顯然抹掉了不同改編之間的差異。林黛玉、賈寶玉、晴雯、劉姥姥……當我們去想象紅樓中人,腦子里浮現的好像都是這一版的角色形象,他們的神情、面容和氣質。參加《紅樓夢》拍攝也改變了演員的人生:飾演林黛玉的陳曉旭皈依佛門,張靜林因為飾演晴雯改名安雯,飾演薛寶釵的張莉多年來一直在微博上分享她和已故姐妹陳曉旭的故事。陳曉旭還曾在14歲時寫下一首詩,《我是一朵柳絮》,“我是一朵柳絮,長大在美麗的春天里,因為父母過早地把我遺棄,我便和春風結成了知己”。字詞間有一種憂郁。也不禁讓人把她和黛玉聯系起來。此外在坊間還流傳著種種演員命運和劇中人物“對應”的故事。只因缺乏出處,這里無法一一贅述。
87版的選角、耗時,以及為劇建造的大觀園都是后來改編無法復制的部分;電影電視劇的制作工業趨向于生產“快銷品”,劇情的“起承轉合”也開始短視頻化。而這些還不是重要的區別。
學者陳維昭在朋友圈感嘆,“既然有人可以把《紅樓夢》往死里夸(所謂的經典化),就可以有人把《紅樓夢》往死里玩(所謂的娛樂化),這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這枚硬幣就是《紅樓夢》的工具化”,《紅樓夢》“已無家可歸”。本文是他以《紅樓夢之金玉良緣》的上映為緣起談《紅樓夢》被改寫的命運。為什么說《紅樓夢之金玉良緣》的改編是讓人不滿的,盡管這不是第一次也可能不是最后一次?
被改寫的命運
任何經典的傳播都以“被改寫”作為基本特征,“被改寫”是經典得以永恒的普遍途徑。改寫的具體情形甚為復雜,不過粗略分之,可歸為兩類。
第一類是旨在真實還原經典原貌,準確傳達經典的基本精神,但由于每一位受眾自身的個體性和歷史性,其傳播不可避免地嵌入傳播者的個人烙印,經典已在傳播過程中被改寫。這一類改寫可稱為“延伸性改寫”,它以貼近、“忠實于”原著為基本面貌。在這一類改寫中,經典的精神家園清晰可見。我們會以“是否忠實于原著”去評判這一類改寫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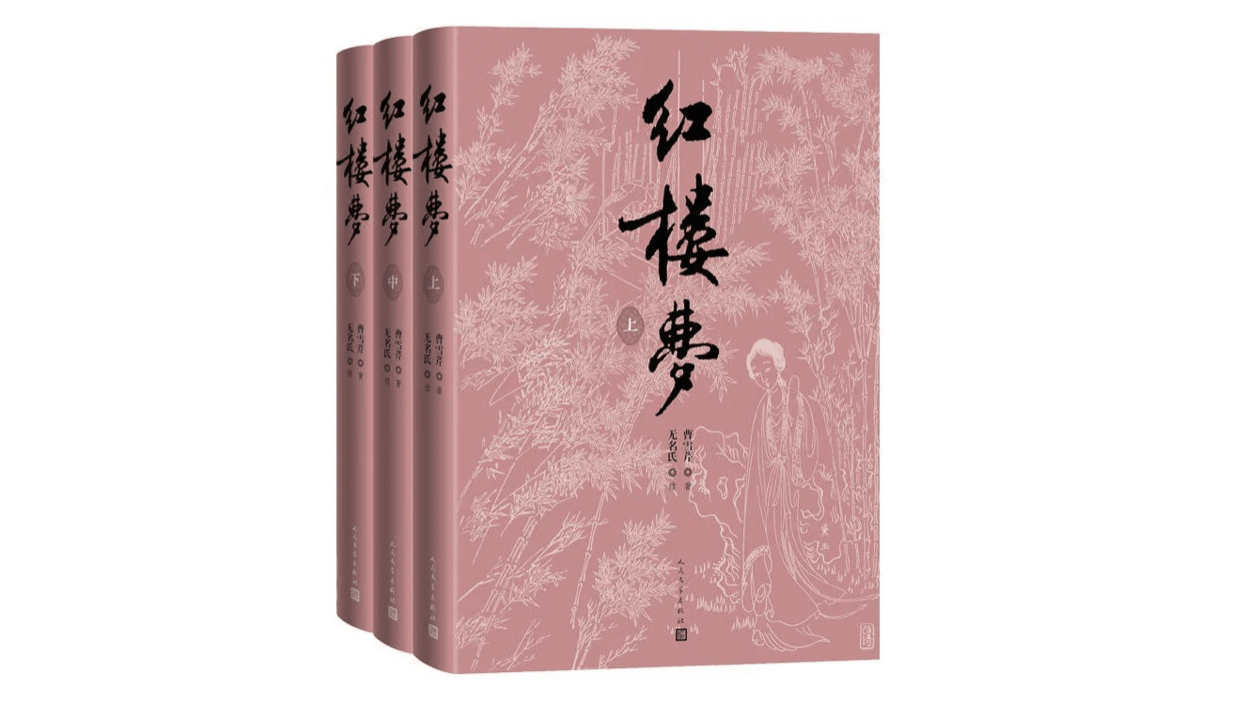
《紅樓夢》,[清]曹雪芹著、[清]無名氏續,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10月。
第二類改寫則是借助經典的文化權威,陳倉暗渡、借筏登岸,借用經典的外殼,把自己的另類思想、情感、嗜好捎帶而出。在這類改寫中,經典的精神家園已被改寫者所淡化、忽略甚至不屑。這一類改寫可稱為“顛覆性改寫”。對于這一類改寫的價值判定,不是看它是否“忠實于”原著,而是看它能否提供某種對人類普遍價值的全新認識。因此這類改寫又分兩種情況,一是通過顛覆性改寫,提供一種具有全新價值的思想認知或情感體驗,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其忠實于歷史的程度于其每一出的時間標示中已見端倪,但劇作最終卻改寫侯朝宗的真實歷史,把他的新朝赴試改寫成出家入道,表達了孔尚任對鼎革時代士人政治抉擇的當代意識,這種顛覆性改寫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顛覆性改寫的另一種情況是出于“票房”“流量”的考慮,借改寫以傳達媚俗的廉價故事,這一類改寫可視為“直播帶貨式改寫”。
《紅樓夢》是一部文學經典,其傳播史雖只有兩百多年,卻同樣經歷了各種各樣的改寫。
作為精英小說的《紅樓夢》
在對各種改寫進行價值評判時,首先涉及我們對《紅樓夢》的經典性的基本理解。
《紅樓夢》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質的書?嘉慶年間蘭皋居士稱《紅樓夢》為“俚俗小說”,今天我們稱它為“長篇章回小說”,均歸之于通俗小說之列。但是,從價值追求、思想表達、情感抒寫的角度看,《紅樓夢》是不折不扣的精英小說。所謂精英小說、精英文化,是指不管這部小說的描寫對象是市井細民,還是貴族世家,作者要表達的,是對形而上價值的追尋,是精神的冥思,情感體驗的反省。曹雪芹以一種形而上的追尋去講述他的故事,以一種高級的隱喻去貫串人物和事件。這個形而上的世界,就是曹雪芹的精神家園。作為精英小說的《紅樓夢》,它與大眾消費文化之間有著天然的拒斥。

曹雪芹畫像(宋惠民繪)。圖片來自中國美術館官網。
《紅樓夢》在敘事上的現實主義風格一直受到讀者的注意,但《紅樓夢》是從石頭(賈寶玉)的角度來敘述故事的,這一點卻必須引起我們重視。只有抓住這一點,我們才能窺見、貼近曹雪芹的精神家園。《紅樓夢》原名《石頭記》,是石頭記下來的故事。賈寶玉反對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不走讀書做官的路,因為“官”就像賈雨村、賈赦、賈政、王子騰之流,小說里寫了他們的負面性,賈寶玉稱他們為“泥做的骨肉”,是骯臟的。為排遣因拒絕主流價值而陷入的孤獨感,他沉浸于青春少女之中,稱她們是“水做的骨肉”,是純潔的。于是有大觀園的故事,有十二釵的故事。長得像女人的男人,也是純潔的,于是有北靜王、蔣玉菡的故事。齡官畫“薔”點醒賈寶玉,大觀園女子之情各有歸屬,這宣告賈寶玉精神樂園的破滅,這是賈寶玉真正的悲劇。賈府最終被抄家,黛玉為寶玉淚盡而亡,履行了第一回那個“還淚”的前世諾言,寶玉已生無可戀,只有出家,回歸大荒山。這就是石頭的敘事立場,離開這個敘事立場,《紅樓夢》就無法回到曹雪芹的精神家園。
最早對《紅樓夢》進行改寫的是程偉元和高鶚的一百二十回本,其后四十回把寶、黛、釵的關系處理成三角戀關系,把其結局改寫成掉包計,建立起“諾言——負心——誤解——死亡”的煽情模式,黛玉臨終前的焚詩稿,尤其是那句“寶玉,你好”的怨恨絕望,讓二百多年來的讀者為之淚奔。這一煽情模式一直為大眾消費文化所熱衷,也為其后大量的《紅樓夢》影視改編者所奉為票房制勝法寶。但陳曉旭認為,黛玉一生為寶玉而哭,淚已還,心愿已了,情字已經看透,她會帶著一顆解脫之心,重回天上,而不會像程高本那樣,讓黛玉帶著對寶玉的一腔怨恨、遺憾離開人世。可以說,陳曉旭已經成功地走進了曹雪芹的精神世界。

陳曉旭在《紅樓夢》(1987)中飾演林黛玉。
《紅樓夢》寫了“葫蘆僧亂判葫蘆案”,賈雨村徇情枉法,寫了王熙鳳殺尤二姐時將都察院等衙門玩弄于股掌之間,暴露了官場的腐敗與黑暗。它寫了大觀園里眾女子之間的明爭暗斗,頗似《甄嬛傳》里的宮斗。它寫了太虛仙姑秘授賈寶玉與可卿以云雨之事,寫了秦可卿離奇的死,再加上“淫喪天香樓”的朱批,艷情文化的解讀呼之欲出。它寫了劉姥姥三進大觀園,展示了村俗文化。寫了倪二、柳湘蓮等小人物,涉及社會下層生活。所有這些,都被統攝于曹雪芹的整體構思之中。
如果把這些內容從《紅樓夢》的整體中抽離出來,把《紅樓夢》改寫成“揭露四大家族罪惡”“艷情”“宮斗”“市井”“寶玉最終為勞動人民所營救”的文學,甚至把《紅樓夢》詮釋為清宮秘史,詮釋為乾隆、和珅與高鶚的政治陰謀,所有這一類改寫,都只能是平庸的乃至惡俗的改寫,屬于“直播帶貨式改寫”。兇殺、暗算、艷情、窺隱、懸疑、以暴制暴、以惡制惡等,是大眾消費文化中的關鍵詞,改寫者一旦想借助于這些關鍵詞去媚俗,其改寫必然會與曹雪芹的價值思考背道而馳。

《紅樓夢》(1987)劇照。
演員的形象、氣質也是內容
在中國古代的文學經典中,《紅樓夢》可以說是最為特別的一部,晚清時期有“開言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是枉然”之說,20世紀初有胡適的“新紅學”,之后又有1954年的“批俞運動”、1973年的評紅運動,《紅樓夢》早已深入人心,廣大讀者對《紅樓》人物早已夢繞魂牽,早已與曹雪芹的精神世界氣息相通。因而每一次的影視改編,其要接受觀眾檢驗的第一關,便是演員的形象、氣質是否符合曹雪芹的設定。演員的形象、氣質是觀眾通向《紅樓夢》精神世界的第一道氛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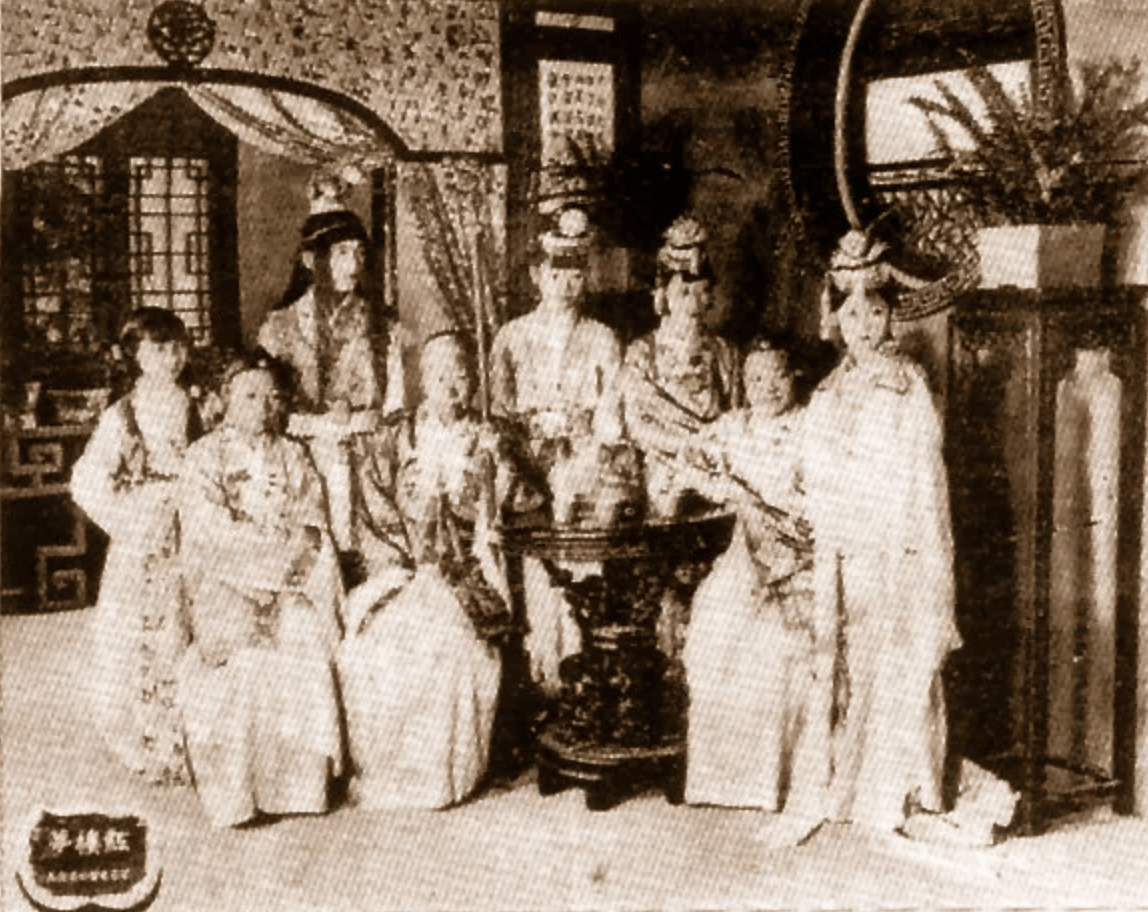
早期銀幕上的《紅樓夢》。圖為《紅樓夢》(1927)劇照。

新版越劇《紅樓夢》(2006)中的寶黛初見。
《紅樓夢》的戲曲、影視改編歷來不乏有影響的作品,但在演員形象、氣質的設定上卻良莠不齊。1958年徐玉蘭與王文娟合作的越劇《紅樓夢》連演54場,盛況空前,它在程高的煽情模式中加入了反抗封建家長包辦婚姻的主題,這是五四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但相對于曹雪芹的價值思考來說,越劇《紅樓夢》已屬離家出走。由于傳統戲曲舞臺的燈光暗淡、舞臺與觀眾之間的距離遙遠,以及越劇演員的反串體制,當時的觀眾對徐玉蘭的扮相并未有太多的不適。

《金玉良緣紅樓夢》(1977)劇照。
1977年李翰祥執導的《金玉良緣紅樓夢》,在第十五屆金馬獎和第二十四屆亞洲影展上都獲得了最佳美術設計獎。該片選取《紅樓夢》中寶黛愛情的幾個片斷,如黛玉進賈府,寶玉摔玉,黛玉葬花,寶玉挨打,黛玉寫《秋窗風雨夕》,然后就是掉包計,黛玉死,寶玉哭靈,賈府被抄,寶玉出家。今天看來,該片實屬平庸,故事的改編雖未背離《紅樓夢》,卻不具備藝術上的感染力,更未提出有價值的思想或獨到的情感體驗。作為林黛玉扮演者,張艾嘉在片中站無站姿,躺無躺態,只具備道具上的功能。但該片演員陣容頗具票房號召力,它在當時的轟動與獲獎,既與其明星效應有關,也與瓊瑤文學模式在當時的風行有關。實際上,那種把感情表達“虐心化”的淺露處理方式有違我們對《紅樓夢》的觀感。
1987年王扶林執導的電視劇《紅樓夢》之所以得到廣大受眾包括紅學專家的認可,首先在于它努力完整地呈現《紅樓夢》的原貌,不僅在故事面貌上貼近原著,而且在氣質上力求神似。這一點,集中體現在演員的選角上。

病中的黛玉。《紅樓夢》(1987)劇照。
我們應該明白,在小說中,無論是寶玉還是黛玉,其神情氣質、舉手投足,不僅僅是憂郁或者癡狂,而且都應該呈現出一種“文采風流”,這種“文采風流”正是《紅樓夢》的精英氣質之所在。電視劇中的陳曉旭和歐陽奮強讓我們感受到了這一點,他們身上那種“文采風流”的氣質,尤其是陳曉旭眼中那種淚光點點、身上那種“文藝范”,讓我們一下子進入了我們所熟知的曹雪芹世界,這在《紅樓夢》的戲曲、影視改編史上可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相比之下,在李翰祥的《金玉良緣紅樓夢》中,我們只看到帥帥的林青霞,卻看不到賈寶玉。李少紅版的小寶玉和胡玫版的寶玉,臉上干凈,卻干凈得蒼白,看不到文化的影子,李版和胡版的林黛玉,其不能讓人認可的,不在于她們是否漂亮,而在于她們都缺乏文采風流的氣質。對“文采風流”氣質的感受,是我們通向曹雪芹精神家園的橋梁。

《曹雪芹》(2003)劇照。
對顛覆性改寫,
人們有更高的要求
魯迅曾說,《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這是在強調讀者的心理定勢對其解讀方向的影響,但這不能成為改寫的隨意性的借口。顛覆性的改寫更需要思想上的創造性和情感體驗上的獨特性。劉鎮偉的電影《大話西游》徹底顛覆了原小說的人物關系和故事的性質,但在中國觀眾的眼中,該片傳達出一種后現代的生存體驗。由于有這種前沿性的價值,觀眾不會去計較該片是否忠實于小說原著。

《大話西游之大圣娶親》(1995)劇照。
當《紅樓夢》改編不追求全面忠實于原著時,而是追求“創新”乃至“解構”“顛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理由對改編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即其改編必須提出具有前沿性的價值思考,必須能對當今遍被華林的思想、情感之霧有獨到的呼吸領會。否則的話,如果只是迎合大眾消費需求,只是為了票房,結果只能改成媚俗的作品。
《紅樓夢》索隱,本質上也是一種改寫。清人把《紅樓夢》索解成“明珠家事”“傅恒家事”,主要出于對豪門秘辛的好奇。蔡元培《石頭記索隱》把“紅”字索解成“漢”字,帶出了清末民初的反清政治敘事,其借《石頭記》捎帶出的“私貨”,具有一定的當代價值。而當闞鐸《紅樓夢抉微》把《紅樓夢》索解為《金瓶梅》的偽裝、把通靈寶玉索解為男性器官時,《紅樓夢》索隱便徹底走向大眾娛樂消費。
1994年,劉心武發表學術小說《秦可卿之死》,其情節基礎是《紅樓夢》里關于秦可卿的描寫和脂硯齋的批語。從寫作藝術來看,這部小說是引人入勝的,是成功的,它對《紅樓夢》中不大連貫的秦可卿故事提出了有新意的別解。但是,這個被抽離出來的秦可卿故事已經遠離了曹雪芹《紅樓夢》的整體藝術思維,而且《秦可卿之死》所蘊含的大眾消費元素值得我們注意,艷情、亂倫、窺秘、懸疑等大眾消費元素是這篇小說的“戲膽”。而這一類小說創作旨趣正是曹雪芹所要超越的。

根據劉心武小說改編的《秦可卿之死》(1999)劇照。
曹雪芹對林如海死后其家財去向并未作更多的明示或暗示,也沒有將此與《紅樓夢》的主要情節或人物相關聯,甚至其家產之豐厚與林黛玉的性格刻畫之間是相矛盾的。清代道光間涂瀛提出了林家財產的問題,說林黛玉葬父來歸,數百萬家資盡歸賈氏,由鳳姐管理。故鳳姐必置黛玉于死地,實為盡吞其財;若黛玉為賈氏婦,則鳳姐需將林家財產歸還黛玉。后來陳大康教授專門寫了《榮國府的經濟賬》討論林家財產的去向問題,從學術的層面推測故事情節中的疑點。但胡玫版的《紅樓夢》即以此為起點,以“陰謀與愛情”為主線去整合大觀園、寶黛婚姻等重大情節,一方面,這悖離曹雪芹《紅樓夢》整體藝術思維,另一方面,這樣的主題切入了“宮斗”“暗算”“懸疑”等大眾消費元素,在思想認知和情感表現上未能給我們提供真正有價值的東西,這才是人們對胡玫版《紅樓夢》最大的不滿。
總之,對《紅樓夢》的改寫,要尊重原著,努力貼近曹雪芹的精神世界和《紅樓夢》的整體藝術思維,回歸《紅樓夢》的精神家園。如果要在《紅樓夢》身上別開生面,別出峰巒,則必須能夠提出有價值的思想認知和深刻的存在體驗,倘能如此,則也可以在另一個層面上與曹雪芹的精神氣質氣息相通。
撰文/陳維昭
編輯/西西
校對/王心







發表評論 評論 (3 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