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聞客戶端 錢江灣

北宋元豐二年,蘇軾因烏臺詩案入獄,寫下《獄中寄子由二首》,其中“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的詩句,恰似一根紅線,貫穿了他與蘇轍四十余載詩文唱和的人生軌跡。自眉山年少時攜手赴京,到中年輾轉八州、貶途隔山隔水,再到暮年相望淚眼婆娑,兄弟二人以詩詞為舟,在宦海沉浮與歲月流轉中,載著“風雨對床眠”的初心,藏著血濃于水的牽掛,將千年兄弟情沉淀為最動人的人間范本與文學豐碑。

一、少年壯志:澠池飛鴻踏雪泥,比翼共赴青云路
嘉祐元年,二十一歲的蘇軾與十九歲的蘇轍,在父親蘇洵的帶領下辭別眉山,踏上赴京趕考的征途。途經澠池,兄弟二人寄宿僧舍,隨性題詩于壁。那時候不過是少年意氣的率性留痕,卻意外開啟了一生唱和的序幕。
嘉祐六年,蘇軾赴鳳翔府任簽判,蘇轍送至鄭州揮別。歸途念及澠池舊事,蘇轍回到京城后寫下《懷澠池寄子瞻兄》:“相攜話別鄭原上,共道長途怕雪泥。歸騎還尋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為縣吏民知否?舊宿僧房壁共題。遙想獨游佳味少,無言騅馬但鳴嘶。”詩中“怕雪泥”的牽掛、“壁共題”的追憶,滿是少年初歷離別時的惦念,字里行間藏著“致君堯舜上”的共同壯志,即便依依惜別,亦對未來滿懷憧憬。

蘇軾收詩后揮筆作答《和子由澠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相較于弟弟的細膩懷舊,蘇軾的和詩多了幾分意境恣逸與通透哲思。
人生漂泊無定,就像飛翔的鴻雁偶然在雪泥上留下爪印,鴻雁飛去后,誰還會計較爪印留在東邊還是西邊?“飛鴻踏雪泥”的妙喻,既預判了仕途的未知,也透著對世事無常的坦然。那些旅途中的艱辛,那些與弟弟并肩走過的崎嶇,早已鐫刻進記憶深處。

這組唱和詩無驚天豪情,卻藏著少年兄弟的靈犀默契。他們那時或許未曾料想,“鴻飛那復計東西”會成為半生寫照,但僧舍中“風雨對床眠”的約定已然生根:待功成名就,便歸隱田園,共聽風雨、同臥閑敘。這份初心,成了此后漫長漂泊中最溫暖的精神慰藉。
二、中年患難:從黃州到儋州,隔山隔水亦相依
黃州歲月,蘇軾“躬耕東坡,筑室雪堂”,清貧中仍筆耕不輟。元豐六年,南堂新葺而成,他即景抒懷,寫下《南堂五首》其二:“暮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顛毛卻未華。故作明窗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意思是我雖已至暮年,慶幸眼力還不錯;常年多病,鬢發卻未曾花白。特意開明亮的窗戶細寫小字,又辟幽靜的房間煉制丹砂,享受這份清靜,詩中盡顯物我兩忘的清虛心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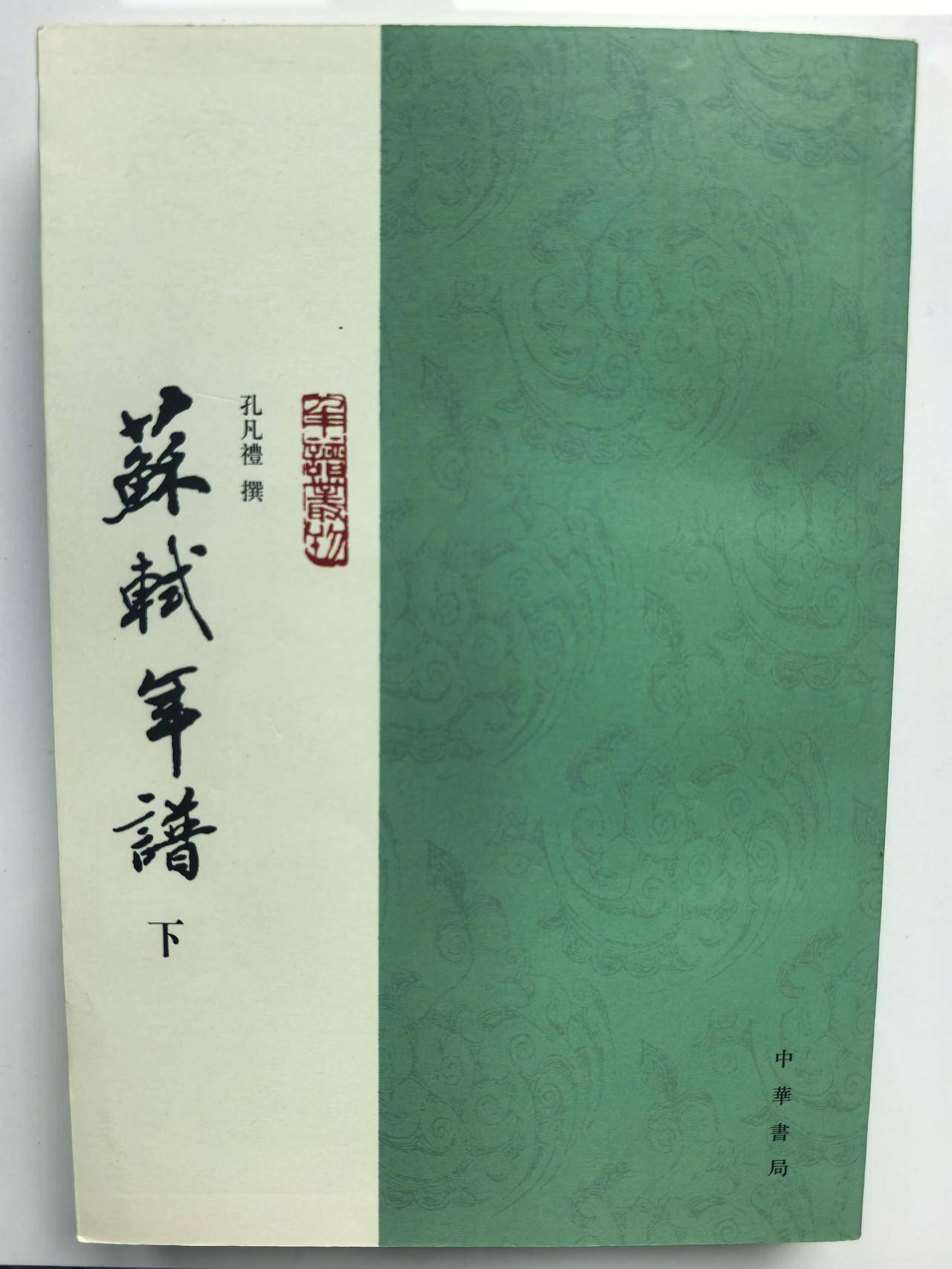
蘇轍得悉兄長境況,寫下《次韻子瞻臨皋新葺南堂五絕·其二》:“旅食三年已是家,堂成非陋亦非華。何方道士知人意,授與爐中一粒砂。”詩中透露出溫馨而略帶傷感的情緒,既表達了對兄弟安穩生活的渴望,也暗含對過往漂泊生涯的感慨。
許多人熟知蘇軾寫于密州的千古名篇《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詞的副標題是“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鮮有人知,蘇轍接到兄長寄來的中秋詞后,所寫的和作《次韻子瞻中秋見寄》:“離別一何久,七度過中秋。去年東武今夕,明月不勝愁……何時共攜手,更把酒杯浮。”意思是我們離別已熬過七個中秋,去年此刻你在東武,我在異地,何時才能再度攜手舉杯暢飲?蘇軾以浪漫馳騁的想象抒懷,蘇轍則以冷靜現實的筆觸,樸素地表達了聚少離多的感慨與重逢的期盼,情感深沉。

紹圣元年新黨執政,蘇軾再貶惠州。嶺南生活艱難,他對子由的牽掛卻從未稍減,作《寄子由》以報平安:“厭暑多應一向慵,銀鉤秀句益疏通。也知堆案文書滿,未暇開軒硯墨濃。湖面新荷空照水,城頭高柳漫搖風。吏曹不是尊賢事,誰把前言語化工。” 詩中刻意描摹閑適場景,實則藏著怕弟弟擔憂的良苦用心。
蘇轍深諳兄長深意,在《次韻子瞻生日見寄》中相慰:“日月中人照與芬,心虛慮盡氣則薰。彤霞點空來群群,精誠上徹天無云。”他在詩中稱贊兄長“內心澄澈、思慮盡消、氣息如蘭”,表達了對其才華與人品的敬仰祝福,也透著自身的豪邁情懷。他時常托人寄送衣物藥品,蘇軾收到后自我調侃:“病中得子由書,寄藥一囊,慰我以不死”,寥寥數字,盡是收到牽掛時的安心與感動。

元符元年,貶謫再升級:蘇軾赴儋州,蘇轍往雷州。茫茫大海隔斷去路,卻隔不斷兄弟情。蘇軾到儋州后,回憶渡海前兄弟同遭貶謫的心境,寫下《吾謫海南子由雷州作此詩示之》:“莫嫌瓊雷隔云海,圣恩尚許遙相望。天其以我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海南與雷州隔著茫茫云海,遙遙相望,上天或許要我將忠義之心留在這偏遠之地。將來誰編寫地理志,海南萬里之地,定會是我真正的故鄉。詩中飽含隔海思念,更展現了逆境中的樂觀精神。

記掛著蘇軾困頓的生活,蘇轍傾盡積蓄托人寄送,蘇軾深為感動。元符三年,他作《過海得子由書》答謝:“經過廢來久,有弟忽相求。門外三竿日,江關一葉秋。蕭疏悲白發,漫浪散窮愁。世事江聲外,吾生幸自休。”詩中描繪秋日蒼涼景象,抒發對世事的超脫之情。這份情誼早已超越尋常兄弟情,成為彼此活下去的勇氣。
三、風雨對床:一生情一杯酒,唱和無盡照初心
元符三年大赦天下,蘇軾得以北歸,蘇轍也復職為“太中大夫、提舉鳳翔上清宮”,遭永州、岳州安置。兄弟倆雷州送別后,終未能再見。次年七月,蘇軾在常州病逝。蘇轍遵兄長遺言,將其安葬于河南郟縣小峨眉山。墓前,他痛哭寫下《祭亡兄端明文》:“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啟手無言,時惟我思。號呼不聞,泣血至地。” 悲慟之中,滿是對“風雨對床”約定終成泡影的無盡悵惘。

蘇軾晚年極崇陶淵明,寫下諸多和陶詩,仿佛與百年前的陶令隔空唱和。他不僅自己唱和,在海南時還邀請蘇轍一同追和陶淵明詩作,并寄去《和淵明歸去來》:“歸去來兮,請終老于斯游。我先人之弊廬,復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漠北,挈往來而無憂。……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詩。賦《歸來》之清引,我其后身蓋無疑。”
那時蘇轍從雷州再貶循州,未能及時與兄長同作。蘇軾離世后,蘇轍整理其遺著,每讀舊作便淚如雨下,特意作《和子瞻歸去來詞(并引)》解釋:“昔予謫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予同作,時予方再遷龍川,未暇也。”隨后,他含悲寫下《追和軾歸去來詞》:“……歸去來兮,世無斯人誰與游?斯人不朽惟知時。時不我知誰為留,歲云往矣今何之?”他贊揚兄長睿智“知時”且“不朽”,悲嘆哲人已逝、形影相吊,情感沉痛。在閑居潁川的最后幾年,蘇轍唯有以追和兄長詩作的方式,延續兄弟間的精神共鳴,踐行“世世為兄弟”的諾言,讓這份情誼在時光中綿延不絕。

縱觀二蘇一生,從少年澠池唱和,到中年患難互慰,再到暮年貶途相望,詩詞唱和始終圍繞“風雨對床眠”的初心。唐代詩人韋應物“寧知風雪夜,復此對床眠”的詩句,一直伴隨兄弟倆,成為漂泊歲月里的精神燈塔。有人粗略統計,僅詩詞唱和(不含文章書信),兄弟二人便近200首。毫不夸張地說,凡是子瞻欣賞過的山河名勝、書作名畫,子由無不在異地“神游”或“次韻”相和。二蘇的唱和詩,早已超越文學作品的范疇,成為兄弟情的見證與載體,每一首都是心靈對話,每一次唱和都是情感共鳴,以詩詞為橋,跨越山海阻隔,抵御宦海險惡,將“兄弟”二字詮釋得淋漓盡致。

如今翻閱蘇軾蘇轍兄弟文集,細細品讀這些詩作,仍能感受到穿越千年的感動。正如周華健在《朋友》中所唱的:“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話,一輩子,一生情,一杯酒……” 蘇軾與蘇轍這對“千年第一兄弟”,用一生證明:真正的兄弟情,是雪中送炭的扶持,是跨越山海的守望,是細水長流的牽掛。“風雨對床四十秋”,這份情藏在“飛鴻踏雪泥”的哲思里,藏在“與君世世為兄弟”的誓言里,藏在“天邊同是飄零客”的相慰里,歷經歲月滄桑依然熠熠生輝,溫暖著每一個讀懂它的人。








發表評論 評論 (1 個評論)